加雷斯·b·马修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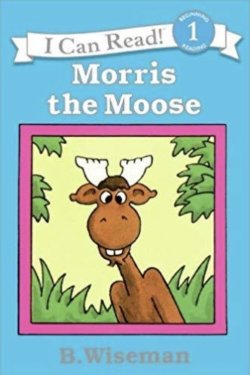
B.怀斯曼对莫里斯驼鹿的评论(学术图书服务,1973)。原发表于《思考:儿童哲学杂志》1(2):2-3。
莫里斯遇到了一头奶牛。“你是一头长相滑稽的驼鹿,”他说。“我是一头母牛,”母牛抗议道;“我不是驼鹿。”莫里斯依然存在。“你有四条腿和一条尾巴,头上还有东西,”他指出。“你是一头驼鹿,”他总结道。“但是我说哞,”奶牛反对。莫里斯不为所动。“我也会说MOO,”他自豪地说。奶牛仍然没有被难住。“我给人们提供牛奶,”她说;“驼鹿不会那样做。”莫里斯仍然不为所动。“所以,”他说,“你是一头给人喂奶的驼鹿。”牛说了最后一点。“我妈妈是一头牛,”她说。莫里斯并不担心。“她一定是一头驼鹿,”他冷冷地回答,“因为你就是一头驼鹿。”
接着,莫里斯和奶牛遇到了一只鹿,它以为它们都是鹿。你可以预测对话的结果。最后,莫里斯、牛和鹿走到一匹马跟前,马向他们打招呼:“你好,你们这些马。”
这个小故事的情节再简单不过了;然而,它提出的问题是非常深刻的。假设有人把驼鹿叫做奶牛?或者马和驼鹿?这有什么错呢?这有什么不对吗?
从一种角度来看,提出的问题是本质属性和偶然属性的区别问题。莫里斯的一个基本属性是莫里斯不能失去的属性;而不停止存在,而且,也许,莫里斯不可能没有。相比之下,意外财产是他可以在不停止存在的情况下失去的财产,也是他可能从未拥有过的财产。
“头上有东西”是成为驼鹿的必要条件吗?对莫里斯来说,是生存的必要条件吗?如果是这样,那么这匹马肯定不是驼鹿。缺角对马来说只是偶然吗?如果是这样,那么莫里斯可能是一匹有角的马。
本质性质和偶然性质的问题是一个元物理问题。它提出的一些问题也可以被认为是分类学的问题——如何对事物进行分类。
要讨论生物分类学,我们需要了解一些关于生物世界的进化和多样性的知识,其中包括什么会与什么交配!然而,人们也可以用非生物学的例子来讨论分类学原理和许多相关的哲学问题。
一天晚上吃晚饭时,我问家人:你们能想到什么问题和下面这些类似,第二:没有一个轮子的自行车是三轮车吗?蛇是没有腿的蜥蜴吗?以下是我得到的一些回答:自行车是没有马达的摩托车吗?老鼠是没有翅膀的蝙蝠吗?没有跑步器的椅子是摇椅吗?裙子是没有上衣的连衣裙吗?
这类异想天开的问题可以用来引入对分类学的实践和哲学问题的深思熟虑的讨论。像驼鹿莫里斯这样令人愉快的思想实验也是如此。
约翰·佩里最近的一篇文章以这样一个故事开头:
有一次,我沿着超市地板上的一串糖,推着购物车沿着高高的柜台一边的过道往前走,又从另一边的过道往回走,想让那个拿着破袋子的购物者告诉他,他弄得一团糟。每绕着柜台走一圈,痕迹就变得越来越厚。但我似乎无法赶上。我终于明白了。我是我想要抓住的顾客。
佩里用这个故事提出了关于信仰逻辑的有趣问题。当(假设上面的故事是关于我的)我开始相信我是制造混乱的那个人时,我的信念到底是什么?它不是那种认为当天超市里唯一的哲学家是那个把东西弄得一团糟的人的信念,因为我可能拥有第一种信念而没有意识到我是超市里唯一的哲学家。也不是相信加里·马修斯是制造混乱的人,因为我可能意识到我是制造混乱的人,却不知道(也许是因为我患有健忘症)我就是加里·马修斯。
佩里也可以用这个故事来引出另一个哲学难题。怎么可能像故事中那样,我“找那个破袋子的购物者,告诉他他弄得一团糟”?如果这是对的,我就会试图告诉自己,我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因为我就是那个口袋被撕破的购物者。但我不是在寻找我自己,我也不想告诉自己,我把事情搞得一团糟。
佩里的故事可能会让我们想起小熊维尼和他试图抓住一只Woozle。在那个故事里,小猪遇到了正在绕着圈走的维尼。接下来是这样的交流:
“喂!小猪说,“你在干什么?”“打猎,”维尼说。“狩猎什么?“追踪什么东西,”维尼熊非常神秘地说。“跟踪什么?小猪说着走近了。“这正是我问自己的问题。我问自己,什么?“你觉得你会怎么回答?”“我必须等到我赶上它,”维尼熊说……”
维尼的想法是,他必须等一等,看看他发现了什么,然后才知道他在追踪什么,这个想法似乎很有吸引力。假设他发现是一种名为“Woozle”的闻所未闻的新生物在制造这些痕迹。那么他跟踪的就是一只Woozle。当然,事实证明,这些足迹是维尼自己留下的(至少是第一批;当小猪加入他的行列时,小猪自然会添加自己的足迹)。但是为什么维尼要等到他“追上了”才说他在追踪的是什么呢?他总是跟不上自己。
维尼真的在追踪自己吗?当然,就连小熊维尼也意识到,追踪自己是愚蠢而徒劳的。那他是在追踪留下这些痕迹的生物吗?但他就是留下这些脚印的生物。
“我一直是愚蠢和迷惑的,”维尼在顿悟的时刻说;“我是一头没有脑子的熊。”也许是这样。但要理解小熊维尼的愚蠢,并弄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是启蒙,即使是最聪明的哲学家也需要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