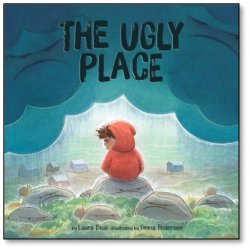
丑陋的地方作者:劳拉·迪尔,插画:艾玛·彼得森
努纳武特:海特传媒公司,2022年
萨曼莎·皮特评论
在爱尔兰哲学家艾瑞斯·默多克的文章《善高于其他概念的主权》中,她警告读者注意人类自我的困境:作为“焦虑的动物”(1970年,第82页),我们倾向于以自私的关心为中心,模糊了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我们忘记了宇宙并不以我们的挣扎开始和结束。我们需要“无私”的时刻——当我们从自己的忧虑中挣脱出来,重新定位自己,看清世界的本来面目的时候。在这篇文章中,默多克讲述了她自己生命中的一个时刻,当时她发现自己被重新定位了。她描述了一段时间,她发现自己处于一种“焦虑和怨恨的精神状态”(1970年,第82页),直到她的眼睛被窗外飞舞的东西所吸引:一只盘旋的红隼。刹那间,她被困住了:“刹那间,一切都改变了。沉思的自我和受伤的虚荣心消失了。现在除了红隼什么都没有”(1970年第82页)。这次邂逅并没有持续太久,但是,当她的注意力转移回她的麻烦时,它们突然变得更小,不那么重要了。这次与自然的相遇,似乎足以让她暂时从自我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劳拉·迪尔将于2022年上映, 丑陋的地方——一个穿着红色连帽衫的小孩——同样心情不好,似乎不太可能自行消退。当他们有这种感觉的时候,他们会做他们总是做的事情:沿着北极海岸线跋涉,参观他们所谓的“丑陋的地方”。他们告诉读者,要达到这个目标,唯一的办法就是你“绝对痛苦”,于是他们把手塞进口袋,怒气冲冲地出发了。

孩子沿着海岸线跺着脚,重复着一句“丑陋”的话。天气,他们告诉我们,是“丑陋的。”岩石很“丑”。鱼很“丑”。连孩子的动作都很难看。它们“在潮池里扔垃圾,溅起水花”,迫使受惊的蜗牛寻找掩护,它们“踢水坑”。插画家艾玛·佩德森利用这种反感,将海滩渲染成泥泞的棕色和阴沉的灰色。岩石和云的插图似乎也反映了孩子的情绪,因为佩德森把它们扭曲成暴躁的皱眉。

有那么一刻,感觉这种忧郁的情绪会永远持续下去。然后,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只海鸥从天际线上滑翔而过。这个孩子注意到了它,和默多克一样,被它的美丽打动了:“它们洁白的羽毛在没有太阳的天空下格外明亮。”孩子的“心安定下来了”。他们记得要呼吸,配合潮水的节奏——进进出出,进进出出。突然之间,一切都变了。阳光透过云层,孩子们透露他们开始感到“更满足”。
突然间,海滩变了样。鱼不再是“丑陋的”,而是友好的,“把水抛向空中,宣布(主角的)到来。”曾经看似猛烈的微风,现在把孩子转了个不停,好像他们在一起跳舞。他们把海虫想象成在表演缓慢的华尔兹。海滩不再丑陋,反而美得惊人。孩子告诉我们:“陆地和海洋提醒我,有很多地方可以发现美。即使在最丑陋的环境下,我们也能一起创造美好。”
人们不禁会把孩子与海鸥的相遇与默多克的红隼相提并论:这是大自然把我们从自我和琐碎的抱怨中解放出来的时刻。正是这只红隼把默多克从她“沉思的自我”中拉了出来(默多克,1970,第82页)。是海鸥提醒孩子要呼吸,要重新考虑周围的环境。默多克和迪尔都让人们注意到,与自然的接触如何破坏了我们的自我中心。是什么让红隼、海鸥——或是一座山、一个瀑布、一场雷雨、一次日落——如此熟练地把我们从琐碎的忧虑中解放出来,迫使我们重新调整思路?这种重新定位是如何在世界上没有任何论点能做到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发生的?
虽然这些瞬间转瞬即逝,但我们中的许多人都能回忆起那些停下脚步,经历无私敬畏的时刻——有时是在大自然中,有时是在艺术中,有时是在另一个人的美丽中。对于试图捕捉这些现象的儿童和成年人来说,这些难以表达的时刻可能会带来一场有趣的哲学斗争,因为即使是最精确选择的词语也可能无法公正地描述这种经历。尽管如此,认识到这些时刻是可能的——而且在伦理上意义重大——为丰富的讨论提供了机会。参与这些自然敬畏时刻的伦理意义是什么?它们如何帮助我们看得更丰富、更仁慈?对社会情绪学习(SEL)感兴趣的教师也可以在Deal的文本中找到丰富的资源,为学生提供关于如何平静他们不安的心灵的具体想法:走向自然,控制他们的呼吸,从新的角度看待世界。
迪尔的《丑陋的地方》为孩子们做了默多克为成人做的事情:强调那些时刻的重要性,通过大自然,我们提醒自己,事实上,我们不是宇宙的中心——因为它比我们的焦虑更广阔、更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