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雷斯·b·马修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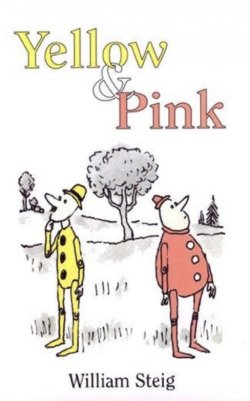
威廉·史泰格《黄与粉》书评(纽约:Farrar, Straus & Giroux出版社,1984)。原发表于《思考:儿童哲学杂志》5(4):1。
两个木头人,一个涂成粉红色,另一个涂成黄色,躺在报纸上晒太阳,也许是为了晒干。他们看起来像牵线木偶。粉红色的那只又矮又胖,而黄色的那只又直又瘦。
每个人都开始怀疑自己在太阳下的报纸上做什么。当黄色注意到他身边的粉红色时,他问道:“我认识你吗?”
“我不这么认为,”Pink谨慎地回答。你知道我们在这里干什么吗?”黄色的问道。Pink不知道。”我们是谁?小黄问。Pink也不知道。“一定是有人制造了我们,”平克猜测道。
黄给平克的假设制造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他自己总结道:“我们是一个意外,不知怎么的,我们刚刚发生了。”
Pink笑了起来。“你是说这些手臂我可以这样那样移动,”他问道,“这个头我可以向任何方向转动,这个,呼吸的鼻子,这些走路的脚,所有这一切都是侥幸发生的?这是荒谬的!”
黄色不为所动。他告诫同伴停下来好好想想。“如果有足够的时间,”他说,“一万年,一百万年,也许是二百五十万年,许多不寻常的事情就会发生。为什么不是我们呢?”
Pink耐心地讲述了他们建筑的一个又一个特点。在每一个案例中,他都向Yellow提出挑战,要求他说明这个特征是如何造成事故的。对于Pink提到的每一个功能,Yellow都试图说明这个功能是如何成为事故的结果的。
最后,一个大胡子男人跌跌撞撞地走过来,检查了一下“粉”和“黄”,满意地宣布:“很好,很干。”当男人把粉红色和黄色夹在胳膊下带走时,黄色在粉红色的耳边低语:“这家伙是谁?”Pink不知道。
在公元前五世纪,恩培多克勒斯推测动物和人类可能是比特和物质的偶然组合,这些组合碰巧能很好地作为单位发挥作用。恩培多克勒斯的思想,以及在他之后的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的思想,都是相当达尔文主义的,只是古人没有遗传学理论来解释一个偶然的片段和部分的组合是如何作为一个整体运作良好的,从而能够自我复制,从而使这种类型得以生存。
柏拉图描绘的是根据永恒的蓝图创造世界和所有居民的工匠大师,他是粉红色的,而恩培多克勒则是黄色的。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至少是粉红色的,同时也是黄色的明显反对者。
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大卫·休谟和查尔斯·达尔文完善了辩论的条件,但他们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在史泰格的故事中,最后那个大胡子男人为平克辩护,尽管平克没有认出他的创造者,也没有意识到他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但史泰格的故事也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故事吗?我们怎么才能知道呢?
黄色和粉红色是一块宝石。没有一个问题,评论或描述性的细节是浪费的。这些插图,也是斯泰格的作品,不仅仅是说明;他们体现了他们帮助讲述的故事。
有人会问这个故事的受众是谁。(总有人这么做。)毫无疑问,这个问题几乎和故事本身的问题“我们是谁”一样棘手和有趣。也许史泰格会说他是为自己写的这个故事。但我要坚持己见,坚持认为他的故事对每个善于思考的成年人来说都是一个儿童哲学家,对每个有抱负的科学家和好奇的孩子来说都是一个初级神学家。
